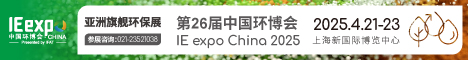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
【 英文 标题】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ANXI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CHINA
【 内容 提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明清以降秦巴山地的讨论是以山区开发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作为核心。本文主要探讨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以期扩展、深化对 历史 上生态环境 问题 的 研究 。
【英文摘要】A major topic in acad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is the development of Qin-Ba muntain areas and its impacts on environme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ast,thispaper deals mainl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ludingit's causes and resul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anxi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China.
【摘 要 题】古代 经济 史研究
【关 键 词】环境保护/陕南/清代/民国
【 正 文】
秦、巴山区是明清时期特别是乾嘉以降我国境内的大规模开垦地区, 社会 经济变迁比较典型,素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环境因素、环境变迁的重视与讨论,该地区再次成为人们考察的重点地区之一,但讨论的核心是山区开发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内容大致涉及:人口迁徙、土地开垦、作物种植、水利兴修、林木采伐、工场造作等,从而使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江河溪流的水文特征发生明显变化、 自然 灾害加剧、环境恶化,其开发史特别是环境恶化也日益为世人所认识(注:如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分别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萧正洪:《清代西部地区的农业技术选择与自然生态环境》,《 中国 历史地 理论 丛》1999年第1期。王元林:《明清西安城引水及河流上源环境保护史略》,该文指出明清西安城引水河流水小沙多与其上源环境恶化有关,“而要解决西安城引水问题就必须恢复上源良好的生态植被”,是呼吁今人以史为鉴,应该“切实保护好河流上源生态环境”,而不是探讨明清时期河流上源是如何展开“环境保护”的。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术界对在此之下所必然出现的环境保护却很少考察,知之甚少。诚然,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不一、学术视野各异,未必都来关心环境保护问题,但在今天环保意识提高、呼声高涨的情况之下只谈当时何以破坏、不讲如何保护,终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笔者以为,这其中与资料的限制不无关系:纵观这些有关秦巴山区的论著,大致上仍以地方志与几种主要的私人著述作为基本史料,而这些资料重在记载各地的风土人物、赋役治安以及作者的兴利除弊之策,环境保护的史料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环保史料更是少之又少,欲从中爬梳寻觅、详细探讨当时当地人的环境保护实在不易,因此还需在此基础上另辟新的资料。有幸的是,在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一套大型的《陕西金石 文献 汇集》正在陆续出版,从而为研究陕西各地特别是晚近以来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详细资料,《安康碑石》与《汉中碑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部(注:张沛辑:《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据该书序言,“安康地区现存的各种碑石,据初步调查,约有二千余通。……本书只收录了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各类碑石二百二十余通”。陈显远辑:《汉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据该书序言,“据初步调查,全区现存石碑,约在四千通以上,……实际收录有一定价值的各类碑石三百四十七通”。可见辑录出版的碑石大致仅占现存资料的十分之一,因此陕南的碑石资料还有可供开拓的广阔天地。),学术界已有人利用此类资料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就包括有明清时期的环境问题(注: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已引录利用了部分资料,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该文是笔者 目前 看到的主要利用上述两部资料研究环境保护的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在这篇长约五六千字的文章里,有关环境保护是全文的三个主要部分之一,约一千八百字,选取了七块碑石资料进行典型 分析 ,正与文题“碑石”对应,但若要从探讨环境保护而言,似应以环保的内容为基准,而将材料仅仅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尽管此前已有该方面的论文出现,但无论从论题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资料的发掘利用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载《汉中师范学报》1999年第2期。又,近来也有人主要利用这两部资料研究了清代陕南的水利与自然灾害,张建民:《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但笔者对以上所有涉及秦巴山区的论文仔细阅读后依然认为,关于当地在大开发之后的环境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究、补充、扩展、完善的必要,这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中有些问题未必仅仅存在于明清秦巴山区的环境研究领域):
一、人们习惯于探讨大开发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但环境恶化并非全由开发所致,尽管开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诱因之一;若要就后者而言,说环境恶化在于开发,那也是在于开发不当,因此开发方式值得特别关注。基于此,减少、杜绝环境恶化也并非是无所作为、弃置封禁,而是因地制宜、合理开发。
二、环境恶化也不仅仅是森林植被与河流水文特征的逆向变化,它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的恶化,在自然环境方面表现为系统失调与生态失衡的动态连锁反应,于是在表面上看来只是森林的逐渐消失,背后却隐藏着食物链的破坏、生物包括某些动物的退化、减少以至灭绝等等,因此对环境恶化的考察应包括自然资源的诸多方面,而且也应包括人文环境如人文景观等等。
三、在今天看来是环境保护之举,但在当时其出发点却是多种多样的,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但在当事人的主观上却并非为、或者严格地说并非皆为环境保护而为;同样,历史上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出台的举措,事实上有一些起不到任何环保的作用。因而需对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作具体分析。
四、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也不仅仅是封山育林、禁止砍伐、保护植被等一味地追求保护、任其自然消长,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环境,故而应该是积极地介入诸如利用、优化食物链等等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保证某些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而且除了对森林植物资源的保护外,还有对其他生物资源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方面的保护。
五、历史上的环境恶化与环境保护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人为的环境恶化未能得到明显的遏制,说明了当时环境保护的有限性,但如何看待某些无奈的破坏与这些有限的保护?如何评估历史上环境保护的当时功效及其对今世影响?
鉴于此,本文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主要讨论清至民国时期秦巴山地之间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虽不能全部解决以上所提出的问题,但毕竟有利于问题的逐步解决。另外,由于该地区晚近以来大开发与环境破坏的典型性,因而当地人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措施,在中国环保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环境破坏与保护的直接原因
生态环境变迁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原因,与人们的环保意识、宗教信仰、社会经济 发展 状况、国家法令制度、人地关系、气候变化、火山爆发等有着密切关系,陕南概莫能外。例如在气候方面,清代中后期基本上仍属于寒冷期(注:可参阅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 科学 出版社,1979年。关于此也有争议与补充,可参阅于希贤:《迁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特别是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研究》的有关综述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根据干湿波动与冷暧变化大致对应这一特点,该时期也处于干旱期,各种植物的垂直、水平分布及其自我更生能力受到影响。而此时适逢人口大量入迁,原有天然资源被大量消耗,且随着人口的机械与自然增长而日益减少(注:终清之世,陕南明显的移民入迁有两次——分别以乾嘉与同光时期为中心。参文:《晚清时期陕西的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从而加大了开发成本,增强了对剩余资源与其他财富的争夺,打破了对资源的适量与有序利用,出现了愈穷愈垦,愈垦愈穷的恶性循环。清人严如煜的《老林说》记载,“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者,今则幅员千里”(注:(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下》,清道光年间刻本,第51页。);在秦岭腹地的孝义,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南山夙称宝山,厅属平平耳,林木之利已尽,即些微药材,采者皆裹粮冒雪,犯险以求,故微利亦甚难得耳”(注:光绪《孝义厅志》卷3《风俗志·物产》,光绪六年刻本,第12页。);位于大巴山之中的镇坪,据道光年间所刻碑石记载,因为“山林树木,恣意砍伐,肆行偷窃,忝然无忌,以致民食艰鲜而俯仰不给”(注:《镇坪抚民分县严禁牲匪赌窃告示碑》,道光九年立石,现存镇坪县白家乡茶店村。《安康碑石》第140~143页。)。不过就该时期陕南的环境破坏而言,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相关:
一、为当时短期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如道光年间石泉县所出现的“淘挖沙金损毁田地”事件,就是一些人只顾淘金而增加收入,从而毁坏了附近的一些良田(注:《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五年立石,现存石泉县中池河卫生院。《安康碑石》第132~135页。)。对秦巴山区森林的滥伐也是如此,留坝紫柏山的不少树木被伐,十年之内,“林木全非”,当局认为“究其故,皆佃户希图渔利,私行转佃,一任砍伐,住持亦从中肥己,以致古木荡然”。指责佃户砍伐谋利,未免偏颇,但渔利肥己,的确指出了其中的重要经济原因(注:(清)俞逢辰:《禁伐紫柏山树木碑》,《留坝厅足征录》卷1《文征》,道光三十年厅志附刊本第35页。)。后来随着天然林地的日益减少、木材需求量增大,就连一些栽种的树木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如陕南著名的水利工程——五门堰在西河坎上栽植的树木,多年以来发挥了护田固堰之功效,但在民国时期先后数次被人盗伐,甚至出现了罚款“尚未呈缴,又往伐树”的失控局面,其主要原因均为“树长成材,木料价高”(注:《五门堰傅青云等认罚赎咎碑》,1920年立石,现存城固县五门堰文物保管所。《汉中碑石》第399~401页。)。
二、过度垦殖及具体生产方式所制约,后者在这里主要是指具体的劳动生产形式。在开垦山地时,即采取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粗放形式,“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①,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注:(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27页。),其中不少是坡度大,不宜耕作的山坡地,初始因焚烧树木杂草,地土尚肥,时隔不长则地力衰退,水土流失,于是迁徙另垦,“数年地薄,则又转徙而之地。今州属(指原兴安州)诸山既尽童矣,迁徙者北咸宁、西西乡,亦不常厥居矣”;“缘山内砂石多而土少,各就有土之处垦种,即于其处结茅栖止,零星散处,迁徙无常”(注: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物产附》,乾隆四十八年刊本。(清)卢坤:《秦疆治略·宝鸡县》,清刻本,第43页。)。某些高寒地区,一般的山区作物也难以种植,如西乡县“西南巴山老林,高出重霄,流民迁徙其中,诛茅架屋,垦荒播种,开辟大半,惟老林之旁,地气高寒,只宜燕麦苦荞,即包谷亦不能种,民食颇为艰窘”(注:(清)卢坤:《秦疆治略·西乡县》,清刻本,第54页。)。垦种及扩展田地面积时,因烧毁植物枝杆而往往引起森林火灾,如在清末安康,“姚光华烧地,烧死漆树无数”,地方上因而出台禁令,要求人们引以为戒(注:《洋溪护漆戒碑》,宣统元年立石,现存岚皋县洋溪乡政府院内。《安康碑石》第356~357页。)。而“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其中“木厂分园木、枋板、猴柴、器具各项”,“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栗、青gāng@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根据树木的大小与种类分别利用,事实上对林木进行全部采伐,“黑河山内木厂砍树之法,树木大小皆用斧伐砍”,彻底破坏了原有植被、导致水土流失。至于当地常见的有相当规模的伐木烧炭,也有火灾隐患,而且其原料往往又是刚刚复苏地方的幼林或成材林,使得这些恢复的植被再次遭到破坏,“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冬春之间,藉烧炭贩炭营生者数千人”(注:(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28页;(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清道光年间刻本,第1页,第4页,第16页。)。实际上不少手工场是从他人租佃而来,“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故具体操作中对林木采取普伐(注:乾隆《洵阳县志》卷11《风俗·物产附》,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如此垦殖采伐之后,昔日青山绿水,几成童山浊溪,“至南山一带,老林开空,每当大雨之时,山水陡涨,夹沙带石而来,沿河地亩,屡被冲压”,田庐受损,河流涨溢,“近山近渭之处,每遇暴雨,非冲开峪口,水势奔腾,沙石冲压地亩,即渭水涨发,漫溢田庄”(注:(清)卢坤:《秦疆治略》蓝田县、华州条,清刻本,第8、31页。)。而且对林木的过量砍伐,破坏了食物链与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会使某些动物逐渐减少、种群退化以至灭绝,而山区对某种动物的大量捕杀,也会导致同样的恶果。有资料记载,在秦岭山区,“鹿,山人猎获甚多”,老虎日益减少(注: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特产》,光绪三十四年刊本,第63页。),起初“野猪践害,贫民远徙”,时隔不长,“野猪稀少”(注:光绪《凤县志》卷1《地理·水利》,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4页。)。此外又如“毒河捕鱼”,不仅毒死鱼类,而且也毒死了其他一些水生资源,破坏了水圈中的食物链,污染了水源。宁陕、砖坪等地都曾出现过此种情况。
三、战争的破坏与影响。如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期间,就有不少树木被毁,“自元年来,教匪滋事,汉南郡县,蹂躏特甚,庙中之地,已瓦砾成堆,松柏为薪矣”(注:《重修武侯庙碑》,嘉庆七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祠。《汉中碑石》第233~234页。)。李蓝起义军与太平军余部在陕南时,由于战争的影响,水利失修,环境恶化,如洋县,“蓝逆蹂躏是邑,祠宇公局尽毁,田地荒芜,堰堤崩坏”(注:光绪《洋县志》卷4《水利志》,光绪二十四年抄本,第11页。),沔县(今勉县),“自同治二年,长毛入境,人民离散,加之过多泥淤石梗,沟渠塞满,堤垠无形”(注:《修复泉水堰碑》,同治五年立石,现存勉县小中坝张鲁女墓亭内。《汉中碑石》第299页。)。战争对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四、制度与政策缺陷。清中央政府无专门的保护森林等与环境密切相关部门与机构(注:赵岗:《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后来对砍伐树木、毁林开垦大多采取放任自流甚至纵容态度,在山区只伐不植,如嘉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曰,“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即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注:《清实录·清仁宗实录》卷53,嘉庆四年十月戊戌,中华书局,1968年,第648页。)。陕西地方当局也对开垦山地态度积极、甚至下达行政命令,如乾隆年间陕西巡抚陈弘谋申饬地方各属开垦山地,“如开垦田地,陕省地方广阔,山坡岭侧未必尽无隙地……凡尔士民当以食指繁多,得业艰难之时,正可以于无主间空山地,端力开种,以广生计,垦得一亩,即有一亩之收,可以养活家口,……如一二年后无收,仍可歇耕,另垦另处”(注:(清)陈弘谋:《陕抚陈公申饬官箴檄》,乾隆《镇安县志》卷10《艺文》,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7~18页。)。再如租佃关系中具体承种者的短期行为、土地使用权分散、主佃间的利益分配等也是影响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陕南“土著人少,所种者不一二。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辄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注:(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27页。)。一些地方“佃客不蓄漆秧、漆树,其意以为怕好地主”,甚至在“芟除杂木草茨”时,“连漆秧一并烧挖”(注:《中河村公议保护漆林药材章程碑》,1915年立石,现存岚皋县洋溪乡中河村。《安康碑石》第363~364页。)等等。
与上述情况相反,一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虽然其最初的出发点未必皆为保护环境而为。在陕南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保护寺庙道观、古树祠墓,美化私人园林,从而部分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风景名胜与文物古迹。这种现象比较常见、普遍,如勉县武侯(诸葛亮)祠、武侯墓,清末与民国期间,汉中府与该县当局均明文予以保护,“(祠内)所有古柏等树、凌霄花,均系汉代旧物,亦令以时灌溉,加以保护,并就隙地栽种成材树木”(注:《汉中府批示武侯祠呈文碑》,光绪七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祠。《汉中碑石》第331~333页。);“其墓前古柏六十余株,森森毓秀,……则侯墓古柏,亟宜爱惜,岂容宵小任意砍伐”(注:《武侯墓定章碑》,1916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墓陵园。《汉中碑石》第393~395页。)。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名胜古迹具有教化抚民、加强统治之功能,官方的重视自在情理之中,而那些寺庙道观,也会不时得到信徒的护养与关照,留坝厅出示禁令保护张良庙周边树木,而傅至@③方丈“生徒满堂,羽流盈室,莳花种竹,雕墙竣宇”(注:《大宗师傅莱宾方丈墓志铭》,1931年立石,现存留坝县张良庙西北二里方丈坟。《汉中碑石》第429~431页。)。城固洞阳宫,“(主持)陈本秀培植风景,栽扦松杉,创修逼火城”(注:《洞阳宫永守清规碑》,1924年立石,现存城固县洞阳宫。《汉中碑石》第414~415页。)。北魏、南宋两度设置在今天南郑的廉水县,至清代道光年间城郭遗迹虽不可考,但“城隍殿宇尚在”,“仪门古柏已数百年物”(注:《重修廉水县城隍庙碑》,道光二十六年立石,现存南郑县廉水乡中学。《汉中碑石》第276~277页。)。私人园林方面,如城固县清初时草莽荒野、颓垣残壁不少,而“皖阳先生之别墅”,“水陆草木之花,错杂交映,应接不暇,中有一古松,挺然高数丈……纵目远眺,则山之高,水之深,迤逦萦绕,接于檐下,恍然非复人世矣”(注:(清)王穆:《游杜园记》,康熙《城固县志》卷10《艺文》,光绪四年刻本,第68~69页。)。
二、风水的考虑。这种情况虽保护范围有限,但一般执行得比较彻底。如白河县即出于风水考虑而禁止垦种山地,该县县城之后山地,被视作“城山”,“至山后来龙所经、有关地脉者,尤不得有所侵损”,因而该处居民开挖耕种,使得“城垣愈卑”,与龙脉有恙,“所关殊非细故”,“虽系民间私业”,也不得随意垦种,否则“以侵毁城池律治罪”(注:《白河知县严禁挖种后山地及随意迁葬坟墓告示碑》,同治七年立石,现存白河县文化馆。《安康碑石》第237~238页。)。现存平利县迎太乡光绪年间所立《迎真寺禁碑》写到,“狮子坝兴平堡为本乡钟毓之气,所关甚广。于光绪六年秋公议:嗣后无论业归何氏,上下周围不得挖毁。特此勒石禁止”(注:《迎真寺禁碑》,光绪八年立石,现存平利县迎太乡迎真寺。《安康碑石》第270页。),即以风水关系不准垦挖。
三、保护当地环境。如防止水土流失以保护水利设施,据光绪三年《留坝厅水利章程碑》记载,当地“每年夏秋雨多之时,山水暴涨,挟带泥沙”,“第坡势既陡,沙脉复松,夏秋雨淋,水沙杂下,殊于渠道有害”,于是规定“禁挖沙坡,以固渠埂也”,“预定岁修,以免壅淤也”(注:《留坝厅水利章程碑》,光绪三年立石,现存留坝县城关镇大滩村。《汉中碑石》第370~373页。)。1948年西乡县政府出示公告,为保护当地重要的灌溉工程金洋堰,其中规定邻近坡地,不得开垦,以保植被,防止水土流失而淤塞渠道,并于堤堰两旁植树护堤,“沿堰渠内外山坡,禁止开垦,藉免沙石淤垫渠道,并在沿堤两旁,栽植树木,以固堰基”(注:《保护金洋堰布告碑》,1948年立石,现存西乡县金洋堰水利管理站。《汉中碑石》第101页。)。官方与民间为保护当地环境而采取的举措在下文中还有不少的例证。
四、维护部分人的财产与既得利益。如留坝对紫柏山树木的保护,官方的解释是,“历系官山,应申官禁”(注:(清)俞逢辰:《禁伐紫柏山树木碑》,《留坝厅足征录》卷1《文征》,道光三十年厅志附刊本,第34页。)。现存岚皋县的道光年间碑石规定,严禁盗窃滥伐,放火烧山,保护财产安全,“柴山竹木,寸草寸物,各有所主。如私砍盗卖及放火焚毁,一经查获,公同处罚,置酒赔山。倘不遵者,亦公同禀究”(注:《双丰桥组碑》,道光三十年立石,现存岚皋县跃进乡双河口原双丰桥头。《安康碑石》第177~186页。)。汉阴县塔岭乡桃园村禁碑写到,“立严禁罚款人汉昌承大耳扒山场耳林壹块,若不严禁拿获,几为众人共置之业,其何以堪。兹此去冬,拿获二人,罚禁山碑一块,请客两席;大洋三元,以给捉贼工资。今而后,如再有肆行无忌,以作损人利己之事,此立有严禁数条,勒之于石,以垂不朽云”(注:《桃园村护耳山禁碑》,1930年立石,现存汉阴县塔岭乡桃园村。《安康碑石》第383~384页。)。又如平利县秋山沟护林条规规定,严禁偷窃毁坏漆秧、漆根,砍伐大小漆树及其他树木,轻者依价赔补,重则送官,以戕害农林条规与盗贼罪惩究(注:《秋山沟公议护林条规碑》,1920年立石,现存平利县秋坪区林管站。《安康碑石》第371~372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自然资源的有序、适时、适量利用,也有利于幼苗的成长。
二、环境保护的主要表现
清代至民国间陕南的环境保护表现在建立制度规章与具体实施等方面,为行文方便,依次 分析 如下:
第一,制定规章制度,明确责权关系,扩大宣传与赏罚力度。
根据现存平利县秋山沟护林碑可知:清代时官方出示禁令,以演戏等形式扩大宣传,民国时农会组织也具有护林职能,当地人砍伐林木后,被罚出资刊碑,重申规定,以儆效尤,“立刻碑永禁效尤人袁世杰、王朝升等情,正月,身子砍伐黎万顺兴栽枞树,被袁姓拿获,报告公团,同众看明,理质不虚,身等自愧无言。况前清禀请牌示,历年演戏,阖境皆知。民国复设农会,保护森林,专为□□起见。……恐年久案遗,身等愿将条规刻石,以做将来不朽之条规列左”(注:《秋山沟公议护林条规碑》,1920年立石,现存平利县秋坪区林管站。《安康碑石》第371~372页。)。这种刊刻碑石的惩处方式在陕南比较普通。
除清代陕甘总督(陶模)在光绪年间有“劝种树谕”外(注:转引自罗桂环、舒俭民:《 中国 历史 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 工业 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冯玉祥在任陕西督军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期间,主持制定《陕甘建设会议议决案》,在其中的《关于造林植树议决案》中规定:“对于已有森林及苗圃切实保护,并择适宜地点添造新林及苗圃。凡私有童山限三年内一律造成新林,逾期得由公家经营之”;“令各县每年于清明节前,按照人口分配植树,并由军、学各界组织植树团,以资倡导”;“另定植树惩奖条例及保护森林条例”。《关于 交通 议决案》规定,“汽车道”、“大车路(省道)”两旁栽植树木,“树距一丈”(注:陕西省档案馆:《冯玉祥对西北开发的史料》,《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
明确责权关系,保证资源的有序利用,加强环境保护。如城固五门堰因水源涵养区的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生成了面积不小的河心夹地,由于所有权归属含混,致使邻近村户前去伐树垦田,后经官方划定权属关系,事遂了息,“本堰上游河心夹地,因数十年河道变更,淤积愈广,估计约足二顷,适当许家庙东偏。前岁除夕,该村无赖数十辈,乘夜将地面树木数百株,尽根刊去,兴工分垦。……构讼至县。经县长楚公尚齐亲临勘验,细考碑粮,始将此段夹地,完全判还本堰管业,随于县署传立专案”(注:《河心夹地碑》,1921年立石,现存城固县五门堰文物保管所。《汉中碑石》第404~405页。)。安康知县为制止滥砍天柱山寺庙林木,明确了与该庙住持、首士等之间的责权关系,“山上树木,不准人窃伐。如有恃强窃伐者,住持将人认清,通知首士,同众查实,送官究治”(注:《安康知县颁布天柱山庙公议章程告示碑》,光绪二十年立石,现存安康市天柱山庙内。《安康碑石》第305~309页。)。光绪年间勉县为保护武侯庙曾规定,“庙中周围之树,住持亦当时常照管,如外人拿获砍树之人,而彼不知觉,以懒惰诛(逐)之。”(注:《重修忠武侯墓碑》,光绪三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墓陵园。《汉中碑石》第326~327页。)
对于破坏与保护者,赏罚分明,现存岚皋县洋溪乡的清代碑石对此有详细规定:“为刊碑戒后、不准烧山砍伐漆树事由。分春姚光华烧地,烧死漆树无数。地主投鸣乡保,经公处断、令姚姓刊碑示众。嗣后如有放火烧山,一被拿获,或被查出,拿者赏工钱八百文,所烧漆树凭人点数,大树一株赔钱八百文,小者赔钱四百文,罚戏一本,公所示众。如赔不起,跪台一日,离庄出境,决不徇情”(注:《洋溪护漆戒碑》,宣统元年立石,现存岚皋县洋溪乡政府院内。《安康碑石》第356~357页。)。这种条规在当地比较常见。
第二、民间力量保护环境、恢复植被,官方对此也予以支持、利用。
陕南当局对勉县民间所拟条规予以确认、公布,保护武侯祠内外文物花木、植树护堤,“陕安道张札开:案据沔县贡生胡丙煊、廪生韩嵘为廪请立案以垂久远事:……谨遵钧谕,酌拟章程十二条,是否有当,相应恳请核定立案。……据此,除批查所议章程,均属妥协,准即如禀立案并候行府转饬沔县,督同刊立碑石,俾资遵守而垂久远”(注:《汉中府批示武侯祠呈文碑》,光绪七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祠。《汉中碑石》第331~333页。)。
利用民间力量,发动捐资捐物,植树种花,保护环境。如道光年间西乡县迫于水患,修堤植树,就是在官民的协力之下完成的,牧马河“曩时岸高河低,去城稍远,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菁开垦,沙泥壅塞,水势亦漫衍无定,逼近城垣”,县令胡廷瑞倡议修堤植树,当地绅商百姓“无不踊跃乐输,共醵钱二万五百七十千有奇,复捐花栗木树二千六百八十余株”,经八个月完成了这一工程(注:《捐筑木马河堤碑》,道光十五年立石,现存西乡县文化馆。《汉中碑石》第266~267页。)。而知县张廷槐更是让“平原之民”轮番监督“北山地主”对“封山之禁”与“护蓄林木”的执行情况(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60《水利四·汉中府·西乡县》,1934年铅印本,第34页。)。
第三、当时陕南人的环境保护集中在植物资源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制止滥砍盗伐,毁林垦植,保持森林资源一定的再生复苏能力。
禁止滥砍乱伐,放火烧山,打击盗窃及其他破坏山林行为,如现存平利县迎太乡道光末年禁山碑写到,“此地不许砍伐盗窃、放火烧山。倘不遵依,故违犯者,罚戏一台、酒三席,其树木柴草,依然赔价”(注:《铁厂沟禁山碑》,道光三十年立石,现存平利县迎太乡铁厂沟。《安康碑石》第176~177页。)。民国时期,汉阴县塔岭乡保护耳山禁碑有更详细的规定,“一禁打柴樵夫,不知自重,擅入境内,枫、柏、耳树,举刀乱砍。拿获给洋五元。……一禁牧牛童子,家长不为早戒,每将牛羊赶入林中,践踏耳秧。拿获给洋三元。……一禁不蓄杂木,有一砍一,有三砍三,查出议罚。……一禁不清火路,春来之时,烧地边、焚渣滓,一举太甚,将耳秧烤坯(坏),此查出,定议培(赔)山”(注:《桃园村护耳山禁碑》,1930年立石,现存汉阴县塔岭乡桃园村。《安康碑石》第383~384页。)。另一些对本家族、本寺庙的山林树木也严禁彻底砍伐,主张适量适时采伐利用,以保护其 自然 更生的能力,如白河县卡子乡东坝口黄氏祠堂同治年间规定,“祠后坐山,只许伐枝自用,务宜禁蓄”(注:《东坝黄氏祠堂禁碑》,同治十三年立石,现存白河县卡子乡东坝口黄氏祠堂。《安康碑石》第248~249页。)。勉县对武侯墓的管理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只许砍树枝、伐枯树、不许以成材树木作为薪材,对于违禁砍伐者予以严惩(注:《重修忠武侯墓碑》载:“每年烧柴,止许(剔)伐树枝,如刊及成材之树,以违议诛(逐)。至于枯树,伐可作材者,亦宜通首事知,若私伐,即系贼盗,无论何人,交值年首事及该乡约,偿酒钱壹千文,私卖者重罚”。光绪三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墓陵园。《汉中碑石》第326~327页。)。上述这些措施,减少了对可更新资源的盲目、过量开采与消耗,从而有利于保护其自我更生能力,延缓或避免了生态恶化,有利于环境保护、维持生态平衡。
2.区分林木用途,以期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保护、扩展 经济 林或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
从陕南现存的大量资料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根据林木的性质与用途,采取不同的开发与利用途径。如名胜古迹处的绿化观赏林与具有文物性质的树木,对于前者时加培植,后者则严加保护。也有供燃料之用的薪炭林,乾隆年间有人即以此类山林捐于安康天柱山寺院,“独是庙貌广大而资费孔多,未尝不叹薪水之艰与养膳之难也。……岁有甲辰,四维山主感天仙之庥,各欢施舍,以祖置之柴山,供庙宇之资用,处明界畔,具约在案,而且誓罚甚切,毋得私砍”(注:《天柱山庙置地碑》,乾隆六十年立石,现存安康市天柱山庙内。《安康碑石》第95~96页。)。至光绪年间,天柱山寺庙又有如此规定,“周围柴扒,只准蓄留,不得刊(砍)伐”(注:《天柱山公议戒律条规碑》,光绪16年立石,现存安康市天柱山庙内。《安康碑石》第294~296页。)。
另外在水利工程如渠堰两旁栽种树木,保护堤坝,如五门堰“新开渠道”,“沿渠栽树扦柳”(注:《五门堰接用高堰退水碑》,1922年立石。《汉中碑石》第406~408页。)。金洋堰灌区人们认为,这类树木具有防护林与风景林的双重性质,严禁砍伐理所当然,“又堰坡一段树木,葱@④蔚然生秀,不特卫护堤防,亦且点缀风景,历禁砍伐,定有条规”(注:《金洋堰重整堰规碑》,1935年立石,现存西乡县金洋堰水利管理站。《汉中碑石》第435~436页。)。民国时期,据称商南县的植桑养蚕与县城绿化初见成效,“知事罗传铭于城外东岗公地二十亩,令植桑一万二千株,又于东西大道及城边周围,植柳一万二千株,油房岭、王家楼两处,私植桑树一千余株,均已采叶饲蚕,丝业日见发达”(注:民国《商南县志》卷6《实业》,1919年刊本,第8页。)。
由于天然森林日趋减少,而对木材等资源的需求又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于是 发展 林业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石泉县号召人们有效利用荒山峻岭,“高山峻岭,虽不可播种五谷,未始不可栽植树木,就所宜之木随处种植,加意培养,如漆如桑如竹如花栗,皆能取利,即橘柑枣梨,省垣每来贩运,亦非无益之物”(注: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道光二十九年刻本,第66页。),紫阳人龙仁昭“寓商于农,播百谷,植树艺,与百工交易”,而“家声丕振”(注:《龙仁昭墓碑》,同治五年立石,现存紫阳县毛坝关盘厢河旧师坝。《安康碑石》第230~234页。)。在此情况下,对经济林或经济价值较高树木的保护更加重视,光绪年间平利县牛王沟对强打漆子、暗伐漆树、盗挖漆秧、偷扒桐子以及抢夺盗窃花木等严加惩治,制定有详细严格的规定(注:《牛王沟公议禁盗碑》的规定可谓至纤至细,在陕南众多的此类碑石中比较典型,其中规定:“一禁、漆子、漆根不得强打私挖,故违者,一经查获,轻则听罚,重则送官。一禁、所栽、所下漆秧,倘有盗窃,一经拿获,鸣公听罚。一禁、明捡枯薪,暗伐漆树、耳树,一经拿获,鸣公听罚。一禁、枸树、枸叶,亦农家出产,不得强采,故违者,查获听罚。一禁、桐子倘一家将捡,九家未打,不得混杂入扒,故违者,查获听罚。一禁、竹笋、花木,草石,不得暗窃明夺,故违者,鸣公听罚”。光绪二十二年立石,现存平利县文化馆。《安康碑石》第312~315页。)。不少陕南人即因违反此类规章而受到惩处,罚款勒石示众,汉阴人纪卓所立《上七里禁山碑》,即属此例(注:《上七里禁山碑》,1932年立石,现存汉阴县七里乡粮食管理所。《安康碑石》第377~378页。)。
3.对于遭到破坏的,则恢复植被,植树种草,退耕还林,以至封山育林。
勉县武侯祠在白莲教起义之后,重新栽种花草树木,“花树竹林,复增其新”(注:《重修武侯庙碑》,嘉庆七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祠。《汉中碑石》第233~234页。)。洋县马良寺及周边环境,在同治初年的战火中遭到破坏,至光绪年间也逐渐得到恢复,“光绪中叶,有好善妇人庞化训之妻李氏,……乐施捐资,推贤募化,不数载,诸神绘彩,各殿重新,筑垣栽柏,@④(浓)荫耸翠,洵胜境也。”(注:《培修良马寺碑》,1920年立石,现存洋县良马寺。《汉中碑石》第401~402页。)
对于坡度较大,不宜耕种的地方,则退耕还林,植树蓄草,恢复植被。留坝厅即采取了此种措施,“禁挖沙坡,以固渠埂也。查荒草坪沟口一带沙坡,逼近渠埂,该处虽异石田,究非沃壤。该地主图见小利,间岁一种,冀得升斗之粮。第坡势既陡,沙脉复松,夏秋雨淋,水沙杂下,殊于渠道有害。今由淇学堂每岁于堰稞项下,津贴该地主稻谷三斗,嗣后不得再行挖种,仍由学堂艺植树木,将来阅时既久,树根蹯结,草长土紧,与渠道大有裨益。仍俟学费充裕,给价承买,以断纠葛”(注:《留坝厅水利章程碑》,光绪三十年立石,现存留坝县城关镇大滩村。《汉中碑石》第370~373页。),这里采取了经济而非行政强制措施来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堰堤,实属难得。
在范围较大地区,则采取封山育林方式以恢复植被。西乡县因山地开垦引起水灾与水土流失,道光三年该县知县曾“劝谕后山居民不许垦种”,后来又有知县张廷槐“封山之禁”,而“北山地主”也“情愿具结,护蓄林木,永不垦种”,张氏为了防止其阳奉阴违,“限各地派出两人轮流每季上山……除查验已栽有各树株不计外,若仍复抗违不栽蓄桐椿花栎各苗,并敢翻土垦种”者,予以严惩(注:道光《西乡县志·水利》,道光手抄本,大概是张氏的举措比较典型,故一百年后,陕西通志对此予以引录,见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60《水利四·汉中府·西乡县》。1934年铅印本,第33~34页。)。也是在道光年间,留坝厅在张良庙一带“蓄禁树木”(注:《重修留候庙暨创建三清殿碑》,道光三十年立石,现存留坝县张良庙。《汉中碑石》第281~282页。)。除此类事例之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更有人出资买地,封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据称当地的生态环境因而得到明显改善,《重修hù@⑤县志》记载,“贺遇林,……幻随其叔父来寄居涝峪口,后以木商起家,积资巨万,村南马尾坡峪,每暴雨发水,村人恒有其鱼之叹,遇林慨然捐钱千缗,买山上下地数百亩,荒为森林,水患遂息”(注:民国《重修hù@⑤县志》卷5《人物义行》,1933年铅印本,第42页。)。
第四、清代至民国时期,陕南人的环境保护还包括对文物名胜、水资源、动物资源、土地资源等的保护。
文物名胜方面,如留坝厅为保护名胜古迹及周边环境,出示禁令:“为查禁事。照得厅境紫柏山留侯祠,为北栈胜区,抱水环山,相峙媲美,所有山林树株,理宜培植茂盛,以壮观瞻”,“为此示仰居民人等知悉,嗣后互相保护,毋许斧斤入山,伤损树株,倘敢仍前侵伐,该乡保住持立即指名送案,以凭究治”(注:《留坝厅禁伐留侯祠树木碑》,道光二十八年立石,现存留坝县张良庙。《汉中碑石》第66页。)。在平利县女娲山三台寺周围,“老桂婆娑,狂夫或恣其攀折;杂植旋绕,窃者或残以斧斤”,于是颁布条规,“庙内桂树,不许往来游人攀折,及所植竹木,不许外来人砍伐”(注:《平利知县颁布女娲山三台寺条规告示碑》,道光二十年立石,现存平利县女娲山女娲庙。《安康碑石》第158~160页。)。而勉县对武侯祠墓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时有条规章程出台,其中民国初年规定,“此后侯之墓场,即著信持勘守。三牌会董,共同照料,如有敢刈一草、伐一木者,该住持立时拿获,报告会董,协同送县,以凭讯办。倘□同徇隐,一并传究”(注:《武侯墓定章碑》,1915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墓陵园。《汉中碑石》第393~395页。)。
水资源方面,治理水污染,保护水资源。其中以金洋堰灌溉区的事例比较典型,不仅通过实践以查找污染源,而且在处理 问题 时能做到经济与环境效益并重。金洋堰是陕南著名的灌溉工程,功效卓著,但道光以至咸丰年间,“每有傍渠陶器,近水烧熬,由是渠坎迭见倾颓,禾稼频遭蚀剥。每逢秧苗正秀,阵阵噫风,叶渐转红,穗多吐白,设醮祷禳,靡神不举,卒莫挽回”,但是至同治初年,因战争 影响 ,“烧熬厂未举,岁遂转凶而为乐。至七八年肃清,烧熬厂复开,岁又转乐而为凶”,后来双方拟定“暂停烧熬厂,以验前言是否,是岁亦遂庆大熟”,因而当地人得出,“年之丰歉,每视烧烧(衍一字)窑厂兴废,历有明征,屡试不爽”,于是“爰集水东绅粮公议,近堰大渠两旁,概不开烧熬窑厂。倘仍蹈前辙,致妨农食,该堰长率领堰夫,掘其窑,毁其窖。如或致酿成讼,该按田亩派钱,以角胜负”。不过当地人也认识到烧熬厂的重要性,未将其彻底关闭,顾此而失彼,而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然货苟无妨于农,货亦人之利用,方且忧其不产,岂可阻其生殖。特患货殖之地,致妨稼啬之事,则革之不利于商,因之有病于农,计惟移之,庶两全无害”,从而既保护了环境,又维护了经济收益与 社会 需要,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此一移也,将见货殖者迁地亦良,务农者崇塘有庆,民食可足,国课有资,利用亦复不缺,所裨岂浅鲜也”(注:《金洋堰移窑保农碑》,同治十一年立石,现存西乡县金洋堰水利管理站。《汉中碑石》第317~318页。)。另外,对灌溉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养护,实际上也是对水资源的保护,“金洋堰旧系累木为堰,严禁刊(砍)伐堰中树木,自古为例”。后又重申这一规定,“念古例不可废坠,仍照旧章,禁止刊(砍)伐堰中树木”,“堰中坡地,倘有窃伐树木,一经拿获,先行理处。如强悍抗违,该禀官究治,决不容情,特勒石以示严禁云”(注:《金洋堰禁止砍树捕鱼碑》,同治十二年立石,现存西乡县金洋堰水利管理站。《汉中碑石》第78页。)。
此外,还有禁止烧山毒鱼等,以制止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与利用,保证人蓄等饮水安全,这不仅是防止水污染、保护水资源,而且是对其他生物资源包括动物资源的保护。地处秦岭山区的宁陕厅于光绪年间曾出示禁令,“照得烧山毒河,大干例禁。虽经前任出告示严禁,乃无知辈藐玩如故,实堪痛恨。……为此示仰关属军民人等知悉,嗣后毋得再行放火烧山、毒河捕鱼,以免致鸟□□□此地饮水□□□□□毒河则饮水之人先中毒。自出示之后,倘□饮□□□,定即从重究办,决不宽恕”(注:《宁陕抚民分府严禁烧山毒河告示碑》,光绪九年立石,现存宁陕县柴家关乡政府院内。《安康碑石》第274~275页。)。大巴山区的砖坪厅也有此类禁令,“烧山毒鱼,故祸生意,……嗣后如蹈前辄(辙),准乡保查明,送案究治”(注:《署砖坪抚民分府严拿匪类告示碑》,光绪元年立石,现存岚皋县民主乡。《安康碑石》第251~154页。)。
土地资源等方面,防止河水冲崩两岸田地,遏制土壤加速侵蚀。如城固县五门堰灌区,马成章、傅乃娃“有五门堰西河坎上水田各一丘,先年被水冲崩,各仅剩田一分有奇,五门堰局绅,见水势直捣,逼近五洞,恐碍堰务,遂与民等田界内坎下,广蓄杨木,藉杀□□(水势),以固河坎”,而马、傅等人“所剩之田”,“赖以保存”,一举两得(注:《五门堰傅青云等认罚赎咎碑》,1920年立石,现存城固县五门堰文管所。《汉中碑石》第399~401页。)。其他如为防止淘金挖沙对附近田地的影响,石泉县于道光年间规定,“淘挖沙金,止许在离田地较远之荒野地方,不许近田地掏挖”(注:《石泉知县整饬风化告示碑》,道光五年立石,现存石泉县中池河卫生院。《安康碑石》第132~135页。)等等。
三、环境保护的效果与局限性
应该承认上述保护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果。如道光年间宁强县的两棵巨大白果树,“遥峰耸峙,上出云霄;翠盖双悬,下荫数亩”,周姓族众欲将其砍伐,因发生争执而未果,后来出卖给黑木林并立碑保护,“自卖之后,许令黑木林人众培补,永留千秋,凡尺枝寸干,周姓不得损败,买主亦不得砍伐”,从而得到保护,至今依然是枝繁叶茂,蔚为壮观(注:《公购白果树碑》,道光二十年立石,现存宁强县庙坝乡白果树村。《汉中碑石》第270~271页。)。又如城固县洞阳宫,道光初年曾出现过住持不守清规、偷卖山场等不法事件,知县俞逢辰“恐外来僧道,偷伐树木,败坏山景”,特命“道人杨教远,即行赴洞阳宫住持,看守香火,经理事务”,此后“不数年,而殿宇皆新,山景颇盛;……所有山场,无人敢伐……而洞阳又为之振兴焉”(注:《洞阳宫山场条规碑》,道光九年立石,现存城固县洞阳宫。《汉中碑石》第57页;又据《文延功果赞并遗嘱条规碑》,道光23年立石,现存城固县洞阳宫。《汉中碑石》第274页。)。但更多的是环境恶化,破坏事件不断。咸丰年间安康兴宁寺为了筹措本金,借贷生息,而将庙中的古柏砍伐变卖(注:《重修兴宁寺碑》,咸丰六年立石,现存于安康市建民乡。《安康碑石》第201~203页。)同治年间勉县武侯墓也出现“住持徐教升不守清规,偷卖古树,私伐皇柏”之事(注:《重修忠武侯墓庙碑》,光绪三年立石,现存勉县武侯墓陵园。《汉中碑石》第326~327页。)。咸宁县志载,“乾隆以前,南山多深林密嶂,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自开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下游渠堰易致淤塞”(注: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1936年铅印本,第5页。)。城固五门堰,清初灌田三四万亩,由于水源补给区环境变迁,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至光绪年间减至两万多亩(注:《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立石,现存城固县五门堰文物保管所。《汉中碑石》第324~325页。)。
汉水从南郑县横贯而过,但由于民国时期水源涵养区的环境恶化,其水文特征也发生了负面变化,“平时宽约半里,一逢暴雨,辄弥漫至四五里”,因无“灌溉之利,故有‘汉不灌田’之谚”(注: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1《舆地》,1921年刊本,第6页。)。不仅水利工程受损,农田庄稼也遭其秧,“南山各谷之水,……时乎夏秋之交,由潦叠洋,百派争流,则裂石奔雷,漂家荡舍,输禾苗于水伯,化膏壤为平沙,何其剧也”(注:民国《周至县志》卷1《地理》,1925年刊本,第23页。)。西乡金洋堰长期以来灌田约计万亩有余,但因河水将“良田冲崩大半”,民国时期灌溉田地减至“五千余亩”,抗日战争时期,“所有堰堤及李五店河潭护成森林,被军民强伐殆尽”(注:《重整金洋堰规碑》,1948年立石,现存西乡县金洋堰水利管理站。《汉中碑石》第451~452页。)。清代中后期以后,有关保护环境的碑石等日益增多,就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原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当陕南大规模地毁林开垦之前,当地的生态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状态,这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强,结构完善,生物体多,生物群落处于正向演替状态。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之后,生物群落处于逆向演替,引起生物数量的增减,某些种类发生改变以至灭绝,因“老林久辟,厚朴、黄莲之野生者绝少”(注:(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山货》,道光年间刻本,第15页。)。“虎,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矣”,“彪,身长腿短,黄尾,形似虎,能食牛,三五年偶一见之”(注: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34年刻本,第63页。)。
从上述的环保措施可以看出,对人文景观的保护胜过对 自然 资源的保护,对后者的保护只是部分的,主要表现在森林资源方面,对动物、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保护比较少见。对林木的保护集中于灌溉区、名胜区与 经济 林或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而对其他地区、其他林木如天然林的保护则相形见绌。一般是民间局部保护或提出申请,要求上级备案予以支持,以保护当地、当事人的利益与所处环境,而官方主动制定、统一彻底的保护措施比较少见。先破坏、污染,后制止、治理,是被动的、不具有前瞻性,而且后者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相对有序与合理利用。保护措施一般是直观的、简单的,甚至是落后的、愚昧的。如道光年间留坝厅对紫柏山林木的保护,除要求住持等具体负责外,对田地的转佃即使用权的转移也加以禁止,“倘敢再任佃户辗转顶拨,侵垦山场,擅伐树木,人问罪,地充公,住持不禀,惟住持是问”(注:(清)俞逢辰:《禁伐紫柏山树木碑》,《留坝厅足征录》卷1《文征》,第35页,道光三十年厅志附刊本。);清末安康县因发生养蚕而争抢桑叶事件,官方不是因势利导、促进蚕桑业的顺利 发展 ,反而出台规定,“无叶之家,不准喂蚕,……违者准饬正、约查实,公同禀究”(注:《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公议禁令告示碑》,光绪二十四年立石,现存岚皋县大道河镇。《安康碑石》第317~320页。),这如同因噎废食,阻碍了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据称西乡县咸丰年间发生“秧苗暗生虫蚀”后,县令亲自祈祷,“灾异遂止”,同治年间邑侯王公“虔诚祷祀,自是虫蚀乃止”,于是众人公议,“厥后设再起虫蚀,必宜仍照前验,禀恳现任邑侯祷祀”,对此荒唐措施深信不疑(注:《前任邑侯王公作祭文祭神灭蝗碑记》,光绪十七年立石,现存西乡县金洋堰水利管理站。《汉中碑石》第346~347页。)。其他地方如蓝田县也祈求神灵“大显神威”来防治蝗虫(注:(清)李元shēng@⑥:《祭告田祖辟蝗蝻文》,《蓝田县文征录》卷1《掌故》,光绪县志本,第9页。)。更有离奇古怪者,认为夏秋多雨、山洪暴发是蛟龙在兴风作浪,又认为蛟龙是野鸡与蛇交配而成,因而防止蛇龙兴作是防治水害的根本,先是陕西巡抚陈弘谋著《伐蛟说》,认为蛟龙“乃雉与蛇当春而交,精沦于地,闻雷声则入地成卵”,主张“用铁与犬血及妇人不洁之衣埋其地以镇之”,定远厅志还引以“事实”为证,“定远自明至今,书大水十有三,半由出蛟为厉,道光三四年受害尤酷”,严如煜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也载有防治蛟龙之法,陕南不少地方志对此予以引录,主张仿效推广(注:以上见,光绪《定远厅志》卷24《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刊本,第4~5页;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26页;光绪《洋县志》卷7《风俗志》,光绪二十四年刊本,第9~10页;民国《佛坪县志》卷下《杂记》,1929年刊本,第9~10页。)。民国年间《续修陕西通志稿》的作者就本地的灾害频繁 分析 总结 到,“南山老林弥望,乾嘉以还,深山穷谷,开凿靡遗,每逢暑雨,水挟沙石而下,漂没人畜田庐,平地俨成泽国,加以黑霜之杀麦,西南风之伤禾,蝗之食苗,蛟之发洪,随时随地层见叠出,自今日 科学 家言之,由防御之不先,补救之无术”(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9《祥异》,1934年铅印本,第1页。)。另外清代中央政府无专门的林木等管理机构,而民国时期对相关环保规定的执行也不彻底坚决,“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期间,政府机构制定了不少 法律 条文。但在当时的 社会 条件上,大多未能有效执行,而仅为具文”(注:罗桂环、舒俭民:《 中国 历史 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 工业 出版社,1995年,第171页。)。陕南地方上虽不时地重申旧章、出台新规,但得到切实执行者寥寥无几。
这一方面是受 时代 局限,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当地的环境状况所决定。简言之,该时期陕南在总体上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闭塞社会,山多田少,森林资源丰富,灌溉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明显,加之人口骤增,自然资源日减,因而集中地出现了对林业资源、水资源的争夺与保护;百姓文化水平低,文物古迹、地方崇拜场所维系教化与基层社会秩序的功能显著,不少成为大众的心灵依托,对其保护因而也比较重视,环保中的功利思想、短期行为明显,清人仇继恒曾感慨到,“盖深岩老林,chǎn@⑦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 目前 ,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日蹙也”(注: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出境货物》,关中丛书本,第47页。),环保在方式 方法 上留于简单、直观。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政策偏颇与阶级局限,如为了保护三台寺庙产,平利县曾规定,“庙内佃户坟墓,只许溜业为界,不得栽蓄树木,以坟占山”(注:《平利知县颁布女娲山三台寺条规告示碑》,道光二十年立石,现存平利县女娲山女娲庙。《安康碑石》第158~160页。),显然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放在次要位置;又如因利益关系没有理顺,也使陕南的漆树栽培受到 影响 ,佃户铲除所租田间的漆秧、漆树,“其意以为怕好地主”,很明显,这种树的存在会影响庄稼生长,而且其本身的生产周期也较长,对佃户不利,所以尽管田主们心照不宣、曲意劝诱,着力保护,但还是屡禁不止(注:《中河村公议保护漆林药材章程碑》,1915年立石,现存岚皋县洋溪乡中河村。《安康碑石》第363~364页。)。
因此可以说,当时的环境保护只是短期内保护了部分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与环境破坏的大范围、持久性相比,其保护还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它只是延缓了当地环境的恶化进程,并未最终摆脱生态恶化的悲惨命运。当然我们也不能抛开当时流民的困窘处境而对其入山垦殖责备求全,山区开发与环境恶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国家无专门机构管理统筹、有的规章制度也得不到切实执行,而秦巴山区的水土流失等环境 问题 正需要全面统筹、综合治理,地方上的、个人的保护与防治只是局部的、短期的、甚至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加之利益的权衡与分配,兴利除弊之不举,官府、地主难辞其咎,“小民狃于目前,难于图始,吏既视为迂远不急之务,一二贤者又惧利未兴而弊已滋,因循岁月,遂致湮废”,使秦岭“溪谷支流及民间汲灌之利不兴焉”(注:嘉庆《咸宁县志》卷10《地理志》,嘉庆二十四年刊本,第5页。),“十年种树,其利不在目前,定难责之棚民、佃户,是在山主之能为远图耳”(注:道光《石泉县志》卷4《事宜附录》,道光二十九年刊本,第66页。)。尽管该时期陕南的环境保护并未最终避免环境恶化,但我们也不能以此作为对其评判的唯一价值取向,先祖们所发出的环保呼声与艰辛的环保历程、以经济方式而非行政命令来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放弃环境保护等等正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陕南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变迁也告诫人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开发,纵有的辉煌也只是暂时的,经验与教训同等重要!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纟加亘
@②原字木加冈
@③原字氵加桂
@④原字艹加隆
@⑤原字雩加阝
@⑥原字日下加升
@⑦原字戋加刂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