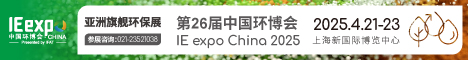垃圾焚烧项目屡遭抵制 政府民众缺乏对话渠道
3月3日,“驴屎蛋儿”(网名)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回来了。
“驴屎蛋儿”本名黄小山,是一位律师,作为唯一市民代表被北京市政府邀请赴日考察垃圾处理技术。
考察团于2月22日从北京出发,成员共七人,除黄小山外,还有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管委”)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整个考察历时10天。
“民意代表”,媒体这样称呼黄小山,政府官员则更愿意称其为“市民代表”。无论哪种称呼,都让这位律师感到压力巨大,中国各地的垃圾焚烧项目在2008年和2009年引发了30多个城市的群体性事件,从而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此次赴日考察,被一些人视为打破中国垃圾处理僵局之旅。黄小山没有这样乐观,就在几个月前,他因为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上街“阻碍了公共秩序”而被拘留。
走出拘留所之后,黄小山和他所在的奥北社区居民选择了一条对抗之外的道路——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雨天“散步”
2009年9月4日上午,黄小山和他的邻居们把50多辆车从北六环开到了东三环农业展览馆。100多名奥北居民穿着蓝色文化衫,上写:“反建阿苏卫,保卫北京城。”
“阿苏卫”来自蒙语“阿速”,意为“守卫”,过去为驻兵所在。现在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附近,即将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奥北社区距这座垃圾焚烧厂的直线距离在3公里以内。居民认为垃圾焚烧会带来二恶英等严重污染,坚决反对。
那天北京阵雨,他们打伞站在“2009环境卫生博览会”的入口前,沉默地举着手中的纸——“坚决要求政府立即执行垃圾分类措施”。博览会的展厅里,有一座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模型。
五分钟内,警车一辆一辆赶到,黄小山看见有人小腿在不住地抖,“大家都很害怕”。
共有七人被拘留,带头的黄小山被第一个带走。
进到“号子”里,黄小山哆哆嗦嗦,头发打着绺,鞋袜湿透。看望他的朋友把现买的线袜子和懒汉鞋从铁门上的小窗里扔进去。“没想到一个律师会有这样的经历。”黄小山苦笑着。
势单力孤的“富人们”
9月4日“散步”之后,奥北人的士气空前低落。政府也同样感受到压力,60周年国庆在即,市管委专门派了四位处长赶到奥北地区“做工作”。
“这种征求意见的工作应该在决定项目之前就做。”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说,“到出了群体性事件之后再做,双方都会不信任。”
之前市政府没有广泛征求过当地居民意见,交流是在上下级之间进行的。北京市政府问昌平区政府,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行不行,昌平区政府提的条件是,可以,但是要拆迁周围2000米内的四个村庄。
奥北居民和四位处长的谈话并不愉快,他们不信任处长们的保证,决定继续向政府施压。
他们认为上次“散步”效果不彰是自己人数太少,于是组织万人签名活动,游说周边楼盘居民加入——在东南方向的下风处,有北京的大型居住区天通苑。再远一点儿,还有另一个大型居住区回龙观。
遗憾的是天通苑居民大多对此事不热心。天通苑距阿苏卫有十几站公交路程,他们闻不到阿苏卫已有的填埋气味,对反对焚烧兴趣不大。
“终于轮到有钱人倒霉了。”奥北人在天通苑论坛上发帖时,甚至收到幸灾乐祸的回复。
阿苏卫附近的奥北地区包括保利垄上、橘郡、汤HOUSE、纳帕溪谷等十几个高档社区,多数房产市值超过千万,在天通苑居民眼中,奥北人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
附近的太阳城老年公寓也曾经是坚决的反建力量,在2009年7月,这一公寓的500名老人曾联名反对昌平区穿过小区修路的计划。在很多维权活动中,老年人往往是中坚力量——他们不怕威胁、有大量时间。
“太阳城的业主们多数是离退休的老人,”奥北居民“佰扶勤”(网名)说,“政府努力做他们的工作,说一些北京垃圾处理的大局,保证安全,很快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相信政府了’。”
“我们也相信政府,但是我们不认为选定的垃圾处理方法是最好的方案。”佰扶勤这样回答那些老人。
另一支可以团结的力量则是官牛坊等村的村民,这些村民多以种菜、养牛、开摩的为生。“我们在等拆迁,或者多得一些‘臭味费’。”村民们有自己的计划。
奥北人第一次觉得自己势单力孤,低密度的别墅本来业主数量就少,有的业主则长年不在北京。“我们最多能聚集上百人,像江苏平望垃圾焚烧厂那样,以大规模散步抗议来叫停这个项目,是根本不可能的。”佰扶勤说。
志愿者的研究报告
奥北人等待着阿苏卫项目开环评听证会的那一天,他们决定,好好准备一份材料。
“至少让我们达到能与支持建焚烧厂的专家对峙的水平。”佰扶勤说。
佰扶勤和“谭嗣同”(网名)开始了奥北志愿者报告的撰写工作,这两位投资业人士可以调整自己的上班时间,行动稍微自由些;其他的居民则全力协助他们搜集资料,提出修改建议和采访专家。他们必须弄清楚焚烧发电厂支持者的每一个观点,并逐条反驳。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此事的一位社区居民就是代理销售垃圾焚化炉的,这让大家对技术细节有更多的了解。
这份志愿者调研报告最终定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从1.0版本开始不断添加新内容,到4.1版本,已经有了39000多字,83个图表、47个尾注和1个视频链接。这份报告被他们转发给一切可能起作用的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两会的代表委员。
报告指出混合垃圾焚烧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提出一套垃圾处理方案:借鉴“MBT(机械生物垃圾处理技术)+RDF(垃圾衍生燃料)”模式;先用机械方式把垃圾进行分类,把能回收使用的部分资源分离出来。其中高热值的部分再加工成RDF,借鉴美国纽约采用铁路运输垃圾的经验,将垃圾衍生燃料作为现有的能源设施燃料加以消化;将处理后的垃圾有机质肥料运送到北京周边地带用于改造沙漠。
“北京周边已经有了沙漠,而阿苏卫以北几公里就有一条不常用的铁路线,如果在那里构筑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分离出来的肥料完全可以运到北京的沙化土地,或者干脆运到内蒙古去改善沙漠,种植薪碳林。”佰扶勤说。
这一处理方案被一些主张垃圾焚烧的专家批评为“乌托邦”,佰扶勤认为这个“垃圾乌托邦”在技术上毫无难度,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协调垃圾处理、铁路公路运输、电力、规划等部门,就不是市管委能处理得了的,至于利用外省的沙漠进行堆肥的设想,更需要由国家统一协调。
不“辩”不成交
去年12月,黄小山被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参加了关于垃圾处理的辩论节目录制(该节目至今未被播出)。在录制现场,他认识了北京市市管委的高级工程师、固体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王维平是被栏目组当作一个“主烧派”专家请来的。
那天,大家在演播厅里争得天昏地暗,广东的居民拿出李坑焚烧发电厂的数据质问“主烧派”,主持人不得不多次请观众和嘉宾平静下来。王维平那天抱病参加,他向激动的市民们强调,“我不是主烧派,我始终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垃圾焚烧确实是一种处理方式,但不是唯一的。”王维平表达完这个意思,黄小山认为王维平和自己有共识,他在录制休息时间找到了王维平,双方交换了联络方式。
辩论结束后,王维平决定去奥北社区见见奥北居民。市管委官员担心王维平的安全——清华大学垃圾处理专家聂永丰教授曾经去海淀区六里屯焚烧发电厂附近和居民对话,遭到了居民的殴打。
“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已经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王维平还是去了。
奥北的居民曾经说他是“王焚烧”“王自焚”,王维平准备做些事情,洗去这些侮辱性的标签。
在纳帕溪谷的温泉游泳池里,王维平和黄小山一起游泳聊天,坦诚相见。
“你进过垃圾焚烧厂么?”王维平问。
“没进过。”黄小山说。
“没见过你就反对垃圾焚烧厂?”王维平说,“找个机会让你好好看看。”
王维平从奥北回来很快给政府提交了建议,“奥北的居民是讲道理的人,老百姓说垃圾填埋场臭,确实是臭,政府要实事求是讲道理,如果连填埋场都管理不好,居民们肯定都会反对垃圾焚烧。”
这个建议提出后,市管委责令垃圾填埋场进行整改,“2000米外不许闻见臭味。”臭味开始有所减少。王维平和奥北人之间的信任增加了。
“往深里说这是民主政治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民主就应该具有协商性,现在的市民和政府没有一个协商机制。”王维平说。
王维平担起中间人的角色,先后五六次去阿苏卫与奥北的居民们沟通,黄小山和其他居民代表也回访王维平和市管委各部门,奥北的“志愿者团队”利用这个契机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和一份垃圾处理方案,并联系了几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请他们和官员交流比垃圾焚烧更好的方案。
在王维平的努力下,市管委决定进行一次对日本垃圾处理机构的考察,王维平更建议邀请黄小山一起去,市管委批准了。接到王维平电话时黄小山正在埃及度假。
“那天我乐得像个孩子,”黄小山说,“老百姓多容易满足啊,哪怕是小小一点积极表示,都会让我们感动很久。”黄小山把好消息告诉了邻居们,“大家提前过年了!”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
临行之前,黄小山在新申请的博客上这样写道:
“临行喝大家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阿苏卫垃圾臭,乡亲们要把门窗关紧喽。……”这篇恶搞版的《红灯记》选段隐隐暴露了他的担心。
黄小山担心“乡亲们”会认为他被“招安”了。“你知道我这几天活得多累么,”黄小山说,“我和他们(其他团员)的关系很微妙,客客气气的,他们对我有点儿信任,又不能完全信任,有些事我得等他们睡了之后才能做。”
黄小山偷偷溜出去过两次,一次去见央视的记者,一次见两位日本垃圾处理专家。
“我托朋友找到了东京的两位固体垃圾处理方面的教授,问我接下来的几天该注意看什么、问什么。”他说。
“第一天我们去了垃圾中转站,”黄小山说,“咱们印象中,这类建筑恨不得200米就能闻见味,但日本的中转站不是,看起来跟北京的国贸差不多。”
“我非常严肃地说一句,那里窗明几净、灯火辉煌,绝对比北京的三甲医院还要干净,我张着嘴进去的,张着嘴出来的。”黄小山说,“日本人把我们拦住换拖鞋才让进。后来参观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换了多次拖鞋。”
同去的市管委工作人员张红樱在自己博文《日本垃圾处理八大怪》里则提到了另一种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服务式的沟通:“游泳馆傍着厂盖”和“二手家具抢着买”。
日本的垃圾处理中心不仅用焚烧垃圾的热量给周围居民提供恒温游泳池水,还修复清洗很多丢弃的旧家具,以极低的价格售卖给周围的家庭主妇。
在国内,法律专业出身的黄小山研究了很久垃圾处理方面的文献,在日本参观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发问,却经常问出令日本人“瞪大瞳孔”的问题。“好专业,好专业。”日本人喃喃地说。
王维平也对黄小山的进步刮目相看,他甚至开玩笑说:“你来考我的博士吧,我说认真的!”
那两天黄小山的生活几乎是连轴转,白天考察回来,晚上写博客。同为考察团成员的《人民日报》记者孙秀艳这样写道:“已经是深夜里,‘驴屎蛋’的手机还不停地响起,国内的媒体还在催着他要素材。”
“我们不能走日本走过的弯路,如果不立法、不分类,就坚决不能进行垃圾焚烧。日本人会把垃圾分成很多类,每类垃圾都由专门的垃圾车运送,车上会写着可燃类、厨余类……而北京的很多小区,放了四个垃圾桶,标注着分类,有认真的人想要分开丢垃圾,垃圾车开过来,也是哗啦一下,把四个桶倒在了一起。” 黄小山说。
在30年前,日本也没有垃圾分类概念,垃圾都是混烧,结果成了二恶英排放大国。后来日本意识到这种焚烧方式的危害,才大规模实行垃圾分类。
“我不相信这是两国国民素质问题,”黄小山说,“我们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垃圾分类,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果前端的处理、分类做好了,后面即使实行垃圾焚烧,大家也不会这么担心了,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黄小山说。
“和平解放阿苏卫”
黄小山回到北京之后,奥北居民们决定好好为他接风,王维平被当作贵客邀请参加,尽管大家可能仍有观点分歧,但王维平已经被奥北人视为朋友。
“你们谁去年骂过我啊?”酒过三巡,王维平笑着对奥北的居民们说。
佰扶勤有点不好意思:“我可能说过您王焚烧,给您起外号不好,但是我没说过您‘王自焚’。”
“那时大家都很激动,对不起王老师了。”大家向王维平敬酒。
市管委决定在“两会”过后拿出考察团的考察报告。黄小山则准备去一趟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看看国内的垃圾焚烧设备情况如何。
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北京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两个已经建成的项目,遗憾的是,这两个单位都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和日本的垃圾焚烧厂相比,中国的垃圾焚烧项目并不欢迎周围居民参观,高安屯运转了一年多,仍然处在“试运行”阶段。农忙时期,高安屯甚至会因为拉闸限电,无法开工。
没有分类的垃圾难以焚烧:北京的垃圾厨余垃圾很多,水分高,这些垃圾很难燃烧,为此曾经出现过“全市优质垃圾支援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情况,别区的优质垃圾送去给高安屯烧,高安屯把不适合焚烧的垃圾送给其他区的填埋场填埋。
对垃圾焚烧炉来说,一旦停电或者垃圾供应不上,停炉和重新启动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大量二恶英。
“请政府先把李坑、高安屯这样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变成垃圾焚烧的‘样板间’,以便让居民安心,”黄小山说。
“也许最后阿苏卫还是会选择焚烧的处理方式,”黄小山说,“但是我们已经发出了声音。希望市管委能够把我们看到的一切汇报给郭金龙市长、黄卫副市长,让他们听取市民的声音。”
佰扶勤说:“我相信民众和政府坐下来交流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日本归来后,知名度暴增的黄小山接到了广东番禺民意代表“阿加西”(网名)的邀请,希望他也能过去帮助达成当地政府和居民的沟通。黄小山兴奋地来邀请王维平,如果“解放”阿苏卫的同时,能够把番禺也顺便“和平解放”了,那真是善功一件。
王维平认真地劝这位比他年轻13岁的朋友:“驴屎蛋,这件事要番禺人自己解决,因为你我都不是当地居民,无法代表他们。我只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我们更不可能代表当地政府,他们必须找到更合适的中间人,来沟通他们和他们的政府。”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