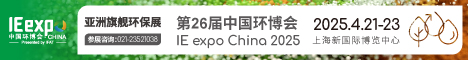两会策划:直面先污染后治理现实
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和教育,“先污染后治理”在民间话语体系里已基本等同于错误的发展模式。然而,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规律,也并非如我们所想那般一无是处。
自然环境既有“生存性功能”也有“生产性功能”,如何最优配置无标准答案
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天生就是冲突的。环境作为一种自然资源,除了具有满足人类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生存性功能”,同时又有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一定的容纳,分界,净化废弃物的空间的“生产性功能”。“污染”这一概念的本质,其实就是“生产性环境功能”降低了“生存性环境功能”的价值。经济模式的选择,意味着要在这两种环境功能之中作权衡和抉择,换句话说,即选择“污染”的程度。如果单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那么取消第二种功能,即停止一切生产活动,自然可以使环境永远保持在最好的状态。但由于环境本身的稀缺性,客服矛盾的办法不可能是消灭其中一个保留另一个,而是要寻求一种组合,使得这两种功能对人类产生的效用综合达到最大。
“先污染后治理说”,便是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种观点。它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得不忍受环境污染,只有当环境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有效地去治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反对才去措施进行处理和防止污染,也不是认为治理污染毫无必要,而是指出在经济水平不高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将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实现,社会需要忍受环境污染的后果。无论是源头防治、过程控制还是末端处理,都是追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最优配置的诸多治理方案中的一种。
“先污染后治理”是追求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规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决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一个充满前瞻性的道路设计,但过去三十年似乎并未很好地贯彻到底。伴随着粗放式制造业加速扩张的同时,中国也进入了环境压力高峰,全国性雾霾天气频现,各项环保指标也不容乐观。中国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走回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超越的体现。
美国环境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就此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某一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不断提高,一个阶段环境污染会加剧;达到污染拐点后,环境质量才会好转。多数研究者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第二产业比例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主要经济活动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转向低污染高产出的服务业、信息业时,生产对环境资源的压力降低;环境破坏和经济发展由此呈现出倒U形的曲线关系。
.jpg) |
环境污染在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都是普遍问题。英国作为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其首都伦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著名的“雾都”。19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世人瞩目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如果不加强环境保护,人类将迎来“寂静的春天”。伺候,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民众意识的提高,环保运动和污染防治才重回正轨。
环境污染是生产的负效应,有生产往往就有污染。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想要推动工业社会的健全发展,关键不在于为了环境杜绝一些限度的污染,而在于如何将污染控制在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让污染物不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避免环境危机的出现。
防控“不可避免的”污染,市场信号比行政命令更灵活高效
传统的“环境政策”,用“环境管控”来概括更为贴切。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当人类社会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时,最早试图通过命令控制和技术工具手段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的环境政策也遵循此道,基本上以政府的行政管控和命令手段为主导,通过国家地区指定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进行直接控制。早在1979年,就曾用“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对污染的排放浓度进行限制,强调污染末端治理。然而由于排污企业被迫接受政府指令,大多采取稀释浓度的做法应对环保部门检查,总体环境质量持续恶化。
向市场讨教如何更有效地防治污染或许是个更好的办法。鼓励通过市场信号作出决策,借助市场力量的政策工具,污染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能导致污染控制目标的实现。市场机制需要最大化的产出,它本身并不会创造更多的污染许可,但是它能创造直接的污染替代物,减少污染的技术、过程和策略,驱使消除污染的东西的价格稳定下降。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便是最好的例子。排污权交易,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即排污权(这种权利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入和卖出,企业因而往往更愿意投入人力物力去开发减少污染的新工艺,节约的污染排放量可以拿到排污权市场上去出售,所得收入可以补偿开发费用,有时还有余。排污权交易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美国总会计师事务所估计,从1990年被用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以来,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明显控制,促进了环境的改善,并节约了约20亿美元治理污染的费用。而后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继实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排污权交易已经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
激烈的环境冲突需要一个更加平等的利益协调机制
市场同样可以为环境冲突提供利益协调机制。中国的环境冲突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自1996年来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十一五”期间,环境信访的件数高达三十多万。自2012年以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轰动社会和网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至少就目前而言,司法手段在冲突的解决上并不更见效。来自环保部信访部门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30多万件的环境信访,行政复议2614件,但行政诉讼只有980件,刑事诉讼只有30件,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一方面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宁愿选择信访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选择司法途径;另一方面司法部门也不愿意受理环境纠纷案件。
利益冲突之所以如此不可调和,在于缺乏一个平等的协商机制。传统的发展模式下,高污染企业往往等同于高税收收入,地方政府乐于招商引资并接受污染企业的转移,而对环境和当地居民造成的外部影响则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这个博弈里,地方政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强势的参与者和利益方。与此同时,作为利益受损者的当地民众,不但没有议价的机会,很多时候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需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无视民众利益诉求,而民众则由不满而转向群体性事件,最后的局面不会是多赢而只能是多输。
一个健全的利益机制,需要政府的退出,而让企业对民众游说、沟通、议价,简单一点说,就是“谈钱”。企业需要这部分环境资源的“生产性功能”,花多少价钱,才能让民众让出部分的“生存性功能”,民众愿意付出多少的价钱,才能让企业把项目“建在你的后院”里。
.jpg) |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邻避运动”,其实也非本国特色,最早曾出现在城市化起步时间较早的欧美国家,后来又出现在日本、台湾等地区。邻避运动在台湾有30多年的历史,早期邻避运动的口号是,“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如今邻避运动在台湾却已不多见,因为政府机关已经慢慢形成一套运作模式,民众也知道应该如何在游戏规则下表达自己的诉求。最能让抗议民众消气满足的,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补偿——“环保回馈”。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设施变得不那么惹人嫌,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此外,还有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
近年来在美国兴建邻避设施遇到的阻力也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其原因在于,国家和联邦机构开始承担批准厂商兴建邻避设施草案的责任,法律允许的程序也提供了更多公众参与邻避设施决策的机会,邻避设施选址方式从“决定-宣布-辨护”开始转向“参与/自愿/合作”。这些,都需要政府进一步的放权,让公众参与到利益机制中去。
与其一边高谈在发展模式上具有前瞻性的、跨越性的创新道路一边持续地对环境只破坏不治理,还不如直面“发展会造成污染”的客观现实规律,运用更灵活的市场手段来实现自然环境“生存性功能”与“生产性功能”的最优配置。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谷腾环保网”